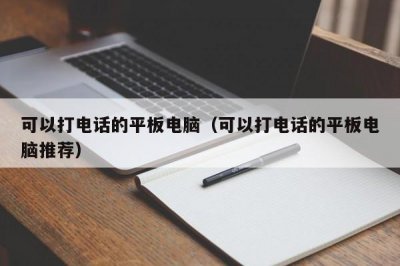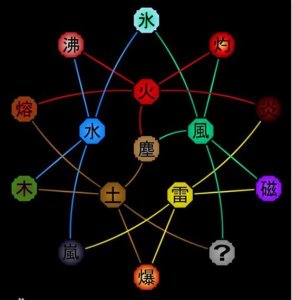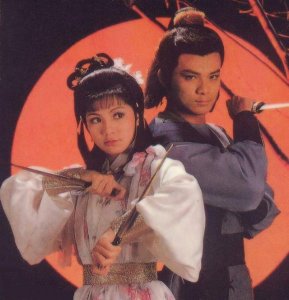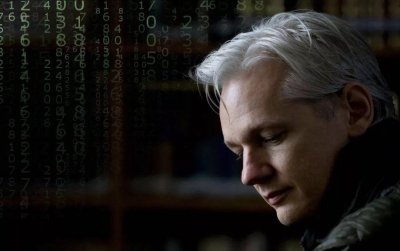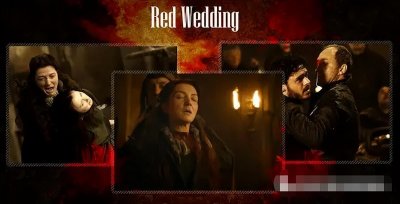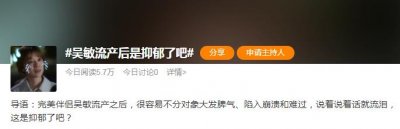新公司法第21条: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法律后果
新公司法第21条: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法律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9日修订通过,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释义】(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王瑞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第36-37页):
股东正当行使权利的要求:一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二是,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三是,行使权利应当符合法律设定权利的目的,不得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例如股东假借行使查阅权盗取公司商业秘密、破坏公司商业计划,则属于不正当行使权利。
【延伸解读】
1.实务中常发生的“股东滥用权利”的情形
(1) 大股东压制小股东:大股东利用表决多数决等方式强迫公司作出有利于己方但有损公司及其他小股东利益的决议。
(2) 利用行使知情权,窃取公司商业秘密:如股东利用其知情权,查阅公司的账务、销售及采购等信息;股东以再增资的名义对公司展开尽职调查;股东以股权转让的名义让拟受让方对公司展开尽职调查等。
(3)法人股东指使其指派的董事、监事作出有利于己方的决议,反对不利于己方的决议,而不考虑这种行为是否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4)享有一票否决权的股东,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权利,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2.有关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司法案例
(1)【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的(2022)京02民终12467号民事判决,裁判要旨:在有限责任公司未作出分配盈余决议情况下,中小股东行使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时,法院应当着重审查以下两点:一是公司缴纳税收、提取公积金后,是否存在实际可分配利润;二是控股股东是否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并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若前述条件无法同时满足,则中小股东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首先,以公司具有实际可分配利润为前提,公司需已按照公司法规定缴纳税收、提取公积金,且具备充足的“自由现金”。
其次,需厘清控制股东滥用权利的具体情形,包括歧视性分配或待遇,变相攫取利润,过分提取任意公积金等行为。
再次,应合理分配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结合双方举证程度,依法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最后,裁判方式上,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具体的盈余分配方案,从而实现对中小股东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的直接救济。
(2)【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5日作出的(2021)豫民终1104号民事判决,裁判要旨:
1.公司盈余利润是否分配是公司的商业判断,本质上属于公司的内部自治事项,通常情况下司法不宜介入。故《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仅规定了只有在公司已通过分配利润的股东会决议后,公司无正当理由未予执行;或公司未通过分配利润的股东会决议,但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司法方有限度的介入公司盈余分配,以适当调整、纠正不公正的利益状态,保护股东利益。法院对公司商业决策的判断应秉持审慎态度。
2.当事人诉请对公司盈余进行分配,人民法院首先应当甄别当事人诉求的分配内容、分配程序及分配目的。公司净资产分配与公司盈余分配在分配目的、实现程序、分配内容上均有显著区别。公司净资产是指属于企业所有,并可以自由支配的资产,为企业总资产减去总负债的余额,包括实收资本(股本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公司如进行盈余分配,应是在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仍有利润的情况下,再由股东会制定分配方案后方可进行分配。
(3)【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的(2021)最高法民申304号民事裁定,裁判要旨: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侵害小股东利益,由此虽导致大、小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冲突,但大股东压迫小股东并非我国法律规定的公司强制解散情形。判断公司应否解散,应当严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之规定判断。
(4)【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4日作出的(2014)合民二终字第00036号民事判决,裁判要旨:对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审查,一方面是程序的合法性审查,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决议内容的合法性审查。公司股东会决议以“补偿金”名义对股东发放巨额款项,在公司并无实际补偿事由,且无法明确款项来源的情形下,此类“补偿金”不符合公司法的“分红”程序,也超出“福利”的一般数额标准,属于变相分配公司资产,损害部分股东的利益,更有可能影响债权人的利益,应依法认定为无效。
(5)【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3日作出的(2020)最高法民再170号民事判决,裁判要旨:《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并未规定股东可以查阅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旨在保障股东查阅权的同时,防止和避免小股东滥用知情权干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在中外股东持股比例相同且合资合同约定合资一方有权自行指定审计师审计合资公司账目的情况下,因审计账目必然涉及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股东知情权的范围不应加以限缩,否则将与设置股东知情权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且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具有不正当目的,故应当允许合资一方查阅包括原始凭证在内的会计账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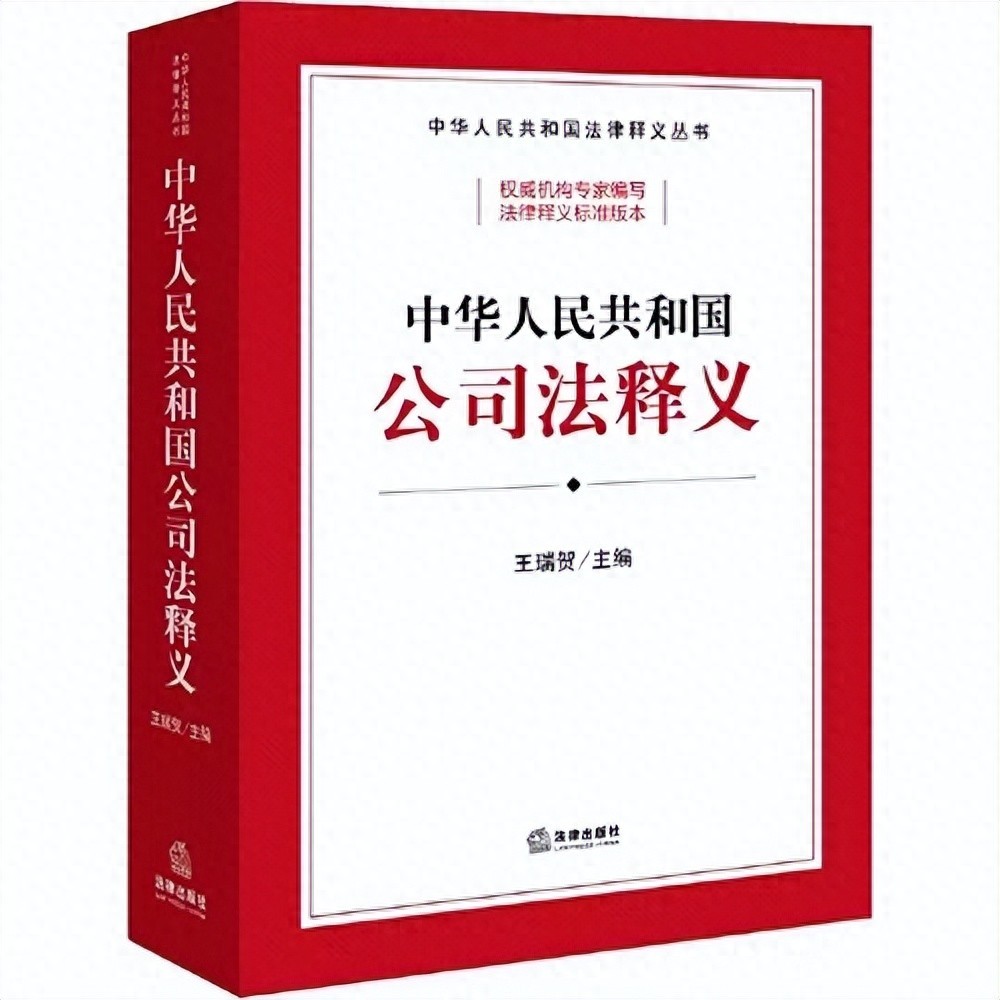
标签: